|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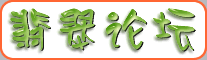 |
 |
加入收藏 使用帮助 联系我们 |
|
|||
|
|
|
||
| 首页 >> 交流区 >> 论坛主区 >> 晓露青晖 >> 查看帖子 |
| |
|
|
||
| ||||
|
| |||
| 文/永宁 红袖添香 “红袖添香”是中国古典文化中一个很隽永的意象,并且无可否认的是非常之美的一种意象。只是今天的人,大约并不了解“红袖”当年是怎么“添香”的。我们所熟悉的“焚香”方式,是点线香。那种装在纸筒里、像挂面似的细细香棒,插一枝在香炉中,点燃香头,就有香烟从香棒上袅袅升起。但是,“红袖添香”绝非拿一枝线香往香炉里插那么简单。 实际上,如果观察古代绘画中表现的香炉,基本上看不到炉中插线香的情况。线香出现的历史相对晚些。在古代生活中,焚香使用的“香”,是经过“合香”方式制成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者散末。明代佚名画家作品《千秋绝艳》中,体现了“莺莺烧夜香”的著名情节。画面上,崔莺莺立在一座高香几前,几上放着焚香必备的“炉瓶三事”中的两件——插有香匙与香箸的香瓶,以及一只小香炉。只是香炉中,崔莺莺的手中,都不见线香的影子。这里是在表现她右手捧着香盒,左手刚刚从香盒里拿出一颗小小的香丸,将要放入香炉中。古代女性“添香”的场景,就这样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不过,“红袖添香”远远不止捻一粒香放入香炉中这么简单。 “焚香”,并不是把香丸、香饼直接加以焚烧;要让香丸、香饼发香,需借助炭火之力。古人追求焚香的境界,是尽量减少烟气,让香味低回而悠长。因此,香炉中的炭火要尽量燃得慢,火势低微而久久不灭。为此,人们发明出复杂的焚香方式,大致的程序是:把特制的小块炭墼烧透,放在香炉中,然后用特制的细香灰把炭墼填埋起来。再在香灰中戳些孔眼,以便炭墼能够接触到氧气,不至于因缺氧而熄灭。在香灰上放上瓷、云母、金钱、银叶、砂片等薄而硬的“隔火”,小小的香丸、香饼,是放在这隔火板上,借着灰下炭墼的微火烤焙,缓缓将香芬发挥出来。古人在谈到销香之法时,总是用“焚”、“烧”、“炷”诸字,但实际上并非把香直接点燃烧掉,而是将香置于小小的隔火片上,慢慢烤出香气。 很显然,焚香的过程相当烦琐。然而,这还不算完事,香一旦“焚”起,还需要不停地加以观察,否则,“香烟若烈,则香味漫然,顷刻而灭”。不过,炭墼或香饼埋在灰中,看不到,如何判断其形势呢?正确的方法是用手放到灰面上方,凭手感判断灰下香饼的火势是过旺还是过弱。于是,唐人诗词中除了“添香”之外,还喜欢描写女性“试香”的情景,描写女人如何“手试火气紧慢”,如和凝《山花子》描写一位女性:“几度试香纤手暖,一回尝酒绛唇光。”添香也罢,试香也罢,在男性文人的笔下,焚香似乎永远和无所事事的女人形象联系在一起。立在香炉前的女性,不论宫词中的失意妃嫔,还是《花间集》中的艺伎,都从来不用为生计操心,她们全部的心思,就是等待某个男人,或者满怀幽怨地思念他,为他的负心而痛苦。摘自《读书》2005年第2期 许多古代仕女画,还有诗文中的描写,给我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以为古代的女性都是把一头长长的青丝盘来绕去,做出许多形状奇妙惊人的发髻来,什么灵蛇髻,坠马髻,犹如乌云出岫,其势巍巍,高耸在女人的头顶上。其实,在很多时代,女性们并不总是这样处理头发的,至少在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不是如此。明代女性最通行的做法,是用髻、云髻或冠,把头发的主要部分,即发髻部分包罩起来。出了嫁的妇女一般都要戴髻,它是女性已婚身份的标志。 不同材料做的髻,则暗示着不同的社会内容。家境一般的女性只能戴用头发编的髻,比如西门庆第一次看到的潘金莲,就是“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有钱人家的妇女,则戴银丝编的髻,也有金丝髻,但不如银丝的普遍。 被底的香球 古代的中国人,特别是贵族阶级,都知道自己及周围环境所散发的气味,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关涉到一个人生活质量的好坏,在这一件事上,现代的中国人倒似乎有不及之处。比如说,对于寝息时使用的卧具,古人就很注意要让它们散发怡人的香气。只要是有足够能力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在使用被褥前,都讲究要“浓薰绣被”。因此,富贵人家,都必备一种叫做“薰笼”的器具,专门用来为衣服、被褥薰香。 在薰笼上薰过的被褥,想来必是深染香氲,闻来沁人心脾的,古人竟然还觉得不够满意。古时令香料充分发挥其性能的最佳办法,是将香料做成香饼、香丸,放置在香炉中的炭火上,通过燃烧的炭火不断熏烤,使香气发散开来。于是,古人不仅在寝室中熏香,在床帐中熏香,甚至还要在被衾中燃香,以达到令衾褥间香氲四弥的最佳效果。为了这个目的,能工巧匠们专门发明了一种可以置放在被下的小香球,以便夜间寝息时,有香球在被褥间不断偷散暗香。唐人制作的这种香球,近年已经发现了不止一件,著名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物中,就有两件涂金缕花银薰球。这种薰球的外壳是个圆球,球壳上布满镂空花纹,以便香气散出。内部的装置则巧妙地利用了重力原理,在球体内装置两个可以转动的同心圆环,环内再装置一个以轴承与圆环相连的小圆钵。在小圆钵中盛放上燃炭和香丸以后,无论香球怎样滚动,小圆钵在重力作用下,都会带动机环与它一起转动调整,始终保持水平方向的平衡,不会倾翻。这种香球既安全又洁净,何况还是在长夜中温暖的被衾下“暗香袭人”,自有一种令人销魂的神秘情味。所以,在中国古代,人们曾经长期保持着夜间用这种香球薰被的习惯。 由于使用起来既安全又干净、便利,所以,香球在古代生活中被派了不止一种用场,并不仅止于浓薰被褥。据《宋史.礼志》,在宋代,“凡国有大庆大宴”,就是在这种最隆重、规格最高的国宴上,设宴所在的殿中不仅要张挂锦绣帷幕,设放兽形银香炉,还要“垂香球”。唐代的香球都是装有银吊链,说明早在唐代,人们就将这种香球悬挂使用了。香球吊挂在半空中,即使偶然发现晃动,它的特殊构造会确保球中的燃炭不会倾翻落下,十分保险。在唐宋时代的宫殿中、华堂上,曾经有镀金的或纯银的香球悬垂在画梁下,镂刻着繁丽花纹的球体金辉银烁,不停地喷芳吐麝,袭袭香氲在殿堂中弥荡萦纡。 《红楼梦》里的玫瑰花香枕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描写说,宝玉“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和芳官一起划拳。像书中的许多细节一样,这个花瓣装成的枕头显得太美了,美得让人怀疑,生活中是否真的会有这样讲究的东西。 其实古代贵族生活就是这么精致。在西汉马王堆一号墓中,便出土有一只用天然香草做枕心的华丽枕头,这只枕头的面料奢侈得吓人,用起绒锦、茱萸纹锦和彩绣三种料子拼成,缝成方方正正的枕头里面填满了佩兰,也就是蕙草。蕙草是古代最重要的天然植物香料之一,有很强烈的香气,拿它来充当枕心,做成的枕头既充满芳香,又柔软舒适。可见,用芳草植物做枕心,在中国久已有之,没什么可奇怪的。 不过,到了南北朝以后,各种各样更优质的天然植物香料被开发出来,像蕙草这样的古老香草变得过时了,香枕头的芯子里也有了新内容。唐宋时代,比较流行一种“菊枕”,是用晒干的甘菊花做枕心,据说有清头目、祛邪秽的妙益。倚着这样的枕头读书、与朋友闲谈,是很清雅的享受;枕着一囊杂花入睡,连梦境都是在花香的弥漫中绽开,自然神清气爽,做噩梦的机会减少,睡眠质量提高。所以,古人提倡这种“香花芯枕”,不仅是为了给生活增添诗意,也是保健、养生的一种方式。 利用玫瑰花、桂花等天然香花、香草,让日常起居,乃至自己的身体上,随时散荡着大自然的清气,这本是传统中国的富贵阶级最习惯的做法。《金瓶梅》中宋蕙莲不过是个与西门庆搭上了手的家人媳妇,可是身上佩个香袋儿,也知道在“里面装着松柏儿、玫瑰花蕊并跤趾排草(一种进口香草)”。更有趣的是,潘金莲送给西门庆的生日礼物中有一件兜肚,“里面装着排草、玫瑰花”。这件男子贴身内衣,是在绸面与绢里的夹层之间装了些排草和玫瑰花瓣,穿在身上,自然就会散发花草的淡淡清香。 这两年,传统的肚兜被改造成了夏天的流行时装,受到许多年轻女性的青睐。如果把对传统的借鉴和翻新进行到底,在兜肚上设计个暗层或装饰性纱兜之类的小饰件,让穿衣人可以随时向其中添放些玫瑰花瓣;或者在兜肚吊带上拴个盛满天然香花瓣的小香囊,在热汗淫淫的酷夏,倒不失为一种爽人心神的清新之举。 “羽扇纶巾”的真相 学者们一向认为纶巾是一种头巾。可是,《陈书?儒林传?贺德基》中谈到,因为贺德基冬日衣裤单薄,妇人赠他白纶巾。赠巾之意,自当是助其御寒,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以赠披巾、披风一类服饰为宜,而不应赠头巾。再说,古人最重视头上所戴的巾冠,很难想像男女混用同一种头巾的情况。《晋书?谢万传》中更记载,谢万曾“衣白纶巾”,证明纶巾是一种穿在身上的服饰,而非戴在头上的头巾。 在当时人的眼中,纶巾有着抗拒名教的象征意义,是放达人士们的醒目“标志”之一。我们今日总说“晋人风流”,如果不了解这些细节,恐怕就不容易理解那“风流”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孔子的坐姿 在先秦到唐代前期的这漫长时段里,你如果从一个体面人家的厅堂窗口望进去,多半会看到这家的主人正凭几而坐,这就如同在今天望进谁家客厅的窗口,多半会看到一家人坐在沙发上一样,是最自然和普遍的事情,是最日常可见的生活状态。 我们今天最常用的三个字,“凭”、“居”、“处”,都与古代用几的风俗有关,都来自于人们使用几这一风俗的象形,这就更显出几在古代生活中的重要和普遍。经典中屡屡提到的孔子之“居”,艺术中屡屡出现的这一姿势,可以这样推想:我们伟大的先师,跪坐在席子上,抄起手,把双臂放置在面前的两足几上,身体借势而自然地微微前倾,注意倾听着弟子的疑难发问,并与他们讨论仁、孝、礼、君子这些关键的概念。 唐人甜点——冰酪配樱桃 古人在食樱桃时,流行在新鲜樱桃上浇乳酪以佐味。北朝、唐宋时代提到“酪”、“乳酪”,通常都是指甜酪,也就是半固态的天然奶酪,而非干酪。乳酪既然是凝冻状的,在吃樱桃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样的乳酪像浇卤一样,浇沃到鲜红的樱桃上。以鲜乳酪的肥浓滋润相配初熟樱桃的鲜甜多汁,其口感之美,可想而知。由于蔗糖在唐代成为通行的甜味品,唐人在樱桃上浇乳酪之外,还要加浇蔗糖浆,增加了酪浇樱桃的甜度,使这一道美点臻于完美。 白居易在诗中形容自己享受天子赐的樱桃的情景,说是:将樱桃剥开、去核,盛在盘碗中,浇上乳酪、蔗浆,用小匙舀食。当代家庭中也常用酸奶或冰淇淋浇在草莓等水果上,自制家庭冷甜食,方法与古人相类似。与今天一样,唐宋人用以浇樱桃的乳酪、蔗浆,事先也都要经过冰镇。我们今天在吃水果酸奶、冰淇淋拌草莓一类冷甜食时,往往以为自己是在享受“西式风情”,殊不知,类似的美味,老祖宗早就发明而且享用过了。 |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
这个好。 感谢静香贴出这么多好帖子,其它帖子容我另抽时间细看。 |
 栽竹载松,竹隐凰凤松隐鹤 培山培水,山藏虎豹水藏龙 |
| 这一篇特别好,比现代人类每天用香水“嗞嗞”两下,有意思多了。 |
| [QUOTE][b]下面引用由[u]佩玉的玉儿[/u]发表的内容:[/b] 这一篇特别好,比现代人类每天用香水“嗞嗞”两下,有意思多了。[/QUOTE] 我懒,每天就是“嗞嗞”两下[em04] |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
| [QUOTE][b]下面引用由[u]静日生香[/u]发表的内容:[/b] 我懒,每天就是“嗞嗞”两下[/QUOTE] 呵呵呵呵呵 |
| [转帖]人间书话:红袖添香还是红袖添乱 作者:阎笑古 大凡读书人都知道“红袖添香夜读书”这绝美的诗句,我虽不才也读了几十年书,就楞没遇上红袖也没熬上这红袖添香的美仑美焕的境界,说来却也不免悲哀。吃不着葡萄说说葡萄酸吧,我就想起《史记·孔子世家》里边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故事。我怀疑的是老先生端坐案前屏心静气逍遥于阴阳易数卦相之中,案旁一窈窕淑女就算是没用那香奈尔5号或第五大道香水只是用点蛤蜊油雪花膏之类,然而这红袖美眉磨墨奉茶随侍着,要是先生累了就绕到他的身后替他捶捶腰背捏捏腿脚,或者静静地看着窗外的蛾子乐此不疲的在灯罩上扑楞着,老先生焉能不动凡心!是呵,红袖添香要不添乱那才怪! 不用说红袖添香是那么有诗意,孔老先生没留下诗却是诗歌编辑的老祖宗,那诗三百篇就是他老人家审定的呢!一会倒倒茶水一会挑挑灯花一会点点檀香,红袖飘来飘去倩影晃来晃去,或者在耳边款款细语呵气又如兰,敢问谁就不会心猿意马?意马了又不会动了凡心?一个活色生香的女子依偎着你,名牌裤裤都撇床下去了谁还有心思读什么书。对此梁实秋先生就曾调侃道,红袖添香“反倒会令人心有别注”。梁先生是文化人说了“别注”,要我想则这红袖没准儿是要添乱的。圣人嘛孟子曾比作熊掌,红袖嘛他比作鱼,他说这两样东东“不可得兼”滴。 “红袖添香夜读书”寥然七字营造出丽人夜色书卷暗香,那惹人遐思撩人欲醉的绝美情境,恍若隔世的才子和怀抱着穿一生红袖添一世香的如珠如玉理想的佳人终成眷属。红袖飘然中将玉臂伸出竹窗任那方绣帕在微风中飘然飞荡感受着和煦的春光,或者月华初上红袖立梧桐影中在微凉的秋风中衣袂飘然,看看天色渐晚屋内已燃起了红烛,幽幽的在夜色中飘摇闪亮。红袖拂去了琴台上的香尘,轻轻地拿过琵琶纤纤玉指不经意地拨过那几根弦,流水般的叮咚声溢了出来,而后红袖单手支着腮看着你读着你,给本来读书的那种枯燥无味劳神伤脑的寒窗之苦带来了不尽的韵味和温馨。这种红袖添香带来的愉悦纵是用醉生梦死来形容也不为过了,难怪“红袖添香”这一个古老而美丽的话题,让那些有书缘之人羡煞慕煞在静谧的夜里会一回回梦见书中那些艳丽凄婉的女子从历史深处的某条胡同里露出的一截红袖,会听到从某座幽暗的庭院里弹响的幽怨琵琶。 不过这绝美诱人的诗句,梦在男人之心却出自淑女之手。“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见于清代女诗人席佩兰《天真阁集》附《长真阁集》卷三之《寿简斋先生》诗,“红袖添香夜读书”大约便由此衍化而来,但《清诗别裁》中却没有席佩兰,席佩兰原名蕊珠,字月襟又字韵芬、道华、浣云,因性喜画兰自号佩兰,清昭文(今常熟)人。诗人袁枚女弟子,被袁引为“闺中三大知已”之一。有《长真阁集》七卷,其夫孙原湘也是著名诗人。 “红袖添香夜读书”,这香倘是一粗壮之手添来恐怕还是不行,那么文人便又想出“素手添香”来。说起素手那又是超可爱滴,纤纤玉指嘛。典出汉代《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红袖所添之香也与今之檀香蚊香佛香断断不同,古代最常用的香乃是饼状或丸状,香并非是用来烧的而是用来熏的。在小香炉的底部燃上木炭复以平板隔开,而香饼或香丸置平板上。很讲究的,是为熏香。李清照的醉花阴词里有一句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大约就是说这种吧。 中国的文人苦啊,你看古往今来读书人真能“红袖添香”那般爽的试问可有几人,看古今的文化名人又哪个不是孤守青灯古卷才终有所成。读书人熬夜时身边也不是没有伴读的东西,晋代人孙敬战国人苏秦“头悬梁锥刺骨”他们选择的是绳子和锥子,和红袖比起来这两样东西实在是太缺乏风月情调了。只是熬来了红袖,那书也就不必读了。命中无红袖想红袖,有了红袖不添香还添乱,也是让人郁闷的事。用弗洛伊德的分析是:“艺术家因某些本能得不到满足,便钻进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使潜意识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红袖美啊,天生丽质不说还大大地用什么爽肤水润肤露除皱霜眼霜防晒霜隔离霜日霜晚霜面膜等等,再加上现代医学的人造美女技术,遍地的是汹涌澎湃的温香软玉足以让男人们大大地迷糊起来! “红袖添香夜读书”,读书的必为男人添香的又必为女人,女人会问凭什么你读书要我来添香!在这女权时代,女人不服呀不公平嘛。怎么添香的是我们添乱的还是我们,切,啥世道!其实,“红袖添香夜读书”就如那画中人水中月,是读书人头枕黄粱的清秋大梦。读书是读书与红袖何干?可文人也是人呀,有七情六欲呀!红袖添香也许不会是妻做的事,妻忙着做你的内助忙着操持家务给你生孩子还得上班,有添香的功夫早呼呼去也。老女人或者黄脸婆自然也不行穿上红袖添香也一定会味同嚼蜡,至于青楼酒肆花街柳巷洗头房的女子,银两交讫便要肉帛相见哪还有闲心读书添香,再者说了妓女添香这一新的命题也是谁都不会接受的。 这样一来红袖之添香就会很难,那么让红颜知己来添可否,可家门难进这香依旧没法添。我有一友一日饮酒言及红颜遂大感概:他一同学妻自缢身亡,同学托其电话通知友好告之出殡时间,而吵醒正睡觉的发妻,妻乃大骂。友回之曰:“你看人家多懂事,上吊了!你倒好,这禽流感满世界都是,你连个感冒都不得!”对大多数读书人那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情趣恐怕只能由心中的红颜梦中的情人来成就了,不过红袖添香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比如耄耋之年的老先生娶研究生就是。清人蒋坦的《秋灯琐忆》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秋芙所种芭蕉,已叶大成荫,隐蔽帘幕。秋来风雨滴沥,枕上闻之,心与之碎。一日,余戏题断句叶上曰:‘是谁无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明日见叶上续书数行云:‘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字画柔媚,此秋芙戏笔也。”虽没添香,可一叶芭蕉夫妻唱和也是算得上一段红袖添香夜读书的佳话。另一面,也告诉人们红袖添香还是添乱与红袖无关。 |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
|



|
|
|
|||
|